日内瓦时间12月3日,世界卫生组织(WHO)总干事Tedros Adhanom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基因编辑不能在没有清晰的指南条件下实施,世卫组织正在组织专家研究基因编辑的健康影响,对此需要“非常、非常小心”。当下,全球对基因编辑用于人体试验,普遍缺乏强有力约束。特别是在中国,目前对高新生物技术临床应用,最高级别的规范性文件,仅为一部行政法规,法制约束力有待提升。
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如果把所有的责任均指向某个人,是不客观的,是不公平的,也是于事无补的。为了从根本上杜绝高新生物技术滥用,预防其危害,必须从社会层面深刻反思。
回顾我国高新生物科技临床应用二十年的历程,基因编辑婴儿事件的发生有其必然性,是全社会长期滥用新技术的结果。
我们弱于创造技术,却强于技术滥用:从器官移植到干细胞疗法,从免疫疗法到手术机器人,从试管婴儿到基因编辑,有哪项临床新技术不被滥用过?
器官移植技术滥用,浪费了大量医疗资源,推高了医疗收费,制造了无数因病返贫家庭。
干细胞疗法滥用,使顽疾患者雪上加霜,很多人掏空了钱包,还有的人“原因不明”地死了。
免疫疗法滥用,制造了尽人皆知的“魏则西事件”。
是全社会正视技术滥用的时候了。
改变急功近利的恶习,是全社会的责任:政府重产业发展轻科学监管;学界重硬科技轻人文社科;医院重技术应用轻伦理调整;技术人员重名利轻道义;全社会浮燥、轻狂、追名逐利、红尘滚滚,长期缺乏深刻反思。
文化先进国家(地区)基于对生命健康的深刻理解,对人类命运的关注关怀,对责任道义的坚守坚持,对弱势群体的尊重保护,无不重视生物(医学)技术立法,无不重视这一领域的良法善治。
英国自1961年以来,颁发了多项关于生物技术的立法。
《人体组织法》(Human Tissue Act 1961),1985年《代孕协议法》(Surrogacy Arrangements Act 1985),1989年《人体器官移植法》(Organs Transplant Act 1989 )、1990年《人工授精和胚胎学法》(Human Fertilization and Embryology Act1990),1998年《数据保护法》(TheData Protection Act 1998),2001年《人类生殖克隆法》(HumanReproductive Cloning Act 2001),2003年《人工授精和胚胎学(已故父亲)法》 (Human Fertilization and Embryology(Deceased Fathers) Act 2003),2003年《妇女生殖阻断(毁损)法》(Female Genital Mutilation Act 2003 ),2004年《人体组织法》(Human Tissue Act 2004), 2008年《人工授精和胚胎学法》,这些法规规范着生命科学研究和生物技术应用活动。
至于英国与生物技术相关的案例法、行政法规、技术应用指南、伦理审查程序,更是不胜枚举。
英国如此,法国、德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莫不如此。
相比之下,国内关于生物技术相应的法律法规机制还存在很大改进空间。
对于高新生物技术临床应用的法制调整,我国目前最高级别的规范性文件,只是一部行政法规——2007年《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在其他方面,有的仅仅是一些部委发布的伦理规范,例如2001年原国家卫生部发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2003年国家科技部和原卫生部发布的《人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指导原则》、2016年,原国家卫计委《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的审查办法》。
对此,笔者认为,我国卫生健康基本(立)法应有自己的立场和原则。鉴于《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草案)二审稿》对此问题尚无有力度的回应,建议该法《草案》增加一条:“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高新技术的临床应用,必须依法定程序通过伦理审查。未通过伦理审查的,不得实施。”笔者建议,应该将这条规定融入到相关的法律责任之中,以强有力的法治推动生命健康伦理建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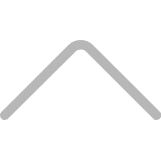
发表评论 取消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