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编辑用于人类辅助生殖是科学界的禁区,这条不可随意逾越的科学伦理红线,因何被贺建奎轻飘飘跨过,把有关生命的诸多难题抛向世人。
与多数科研者的来路不同,贺建奎从香港大学李兆基大会堂舞台的另一侧走上前。
这是“基因编辑婴儿”消息公布后他的首秀,给第二届人类基因组编辑峰会这样一个鲜为人知的学术会议带来了不寻常的热闹。2018年11月28日中午,几乎打断演讲的骚动、排队等待提问的观众,以及主持者Robin Lovell-Badge教授面前一叠写满媒体疑问的卡片,都昭示着研究者贺建奎的“不同”。
走了一条不同的路,贺建奎“火了”。这把火照亮了他自己,但点燃了生物医学整片森林。
11月26日,一个普通的周一,来自深圳南方科技大学的副教授贺建奎声称,一对名为露露和娜娜的基因编辑婴儿已在中国健康诞生。这对双胞胎的一个基因经过修改,使她们出生后即可天然抵抗艾滋病。
这是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发布消息的人民网随后删除,但消息已经迅速发酵,争议和批评随即铺天盖地,贺建奎及南方科技大学等关联方成为众矢之的。
一周之内,中国工程院、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学部,以及122位学者、140名艾滋病研究专家,接连以严厉词句反对贺建奎实验的不伦。被质疑与这项实验相关的高校、医院等机构,轮番否认,极有效率地“击鼓传锅”。几天来,没有机构愿意为他的实验负责。
业界共识是,如果基因编辑婴儿在11月初降生属实,这件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情,酝酿了至少十个月,重锤落地,令人惊悚。但贺建奎面对汹涌质问时,解释虚与委蛇,以艾滋病孩子的健康需求为由,试图为自己正名,对绕过监管、伦理审查的理由避之不谈。无论是上千名与会者,还是更多观看网络直播的普通人,没有谁对他的回答满意。
当被问及为什么要先斩后奏?贺建奎低头略微想了一下,只回答说,三年前就已经与科学界接触,并且已经说了这样一个计划;也与美国的相关科学技术人员进行沟通,在美国,很多专家知道这个事情,他们也是其咨询的对象。
如同一拳打在棉花上,人们带着满腔疑问来,又带着更多疑问回去。这一严重违背伦理的科研事件如何收场?国家有关部门已经公开地严厉表态,会否成为真实的处罚?会有严格法规,避免类似突破伦理底线的科研探索再来吗?
伦理与安全的追问
不是每一项科研成果都会让人兴奋并广受尊敬。2018年11月26日,人类突然被告知迎来一对基因编辑婴儿。猝不及防的,科幻片的诡秘场景成为现实,让人恐惧。
与贺建奎对谈的主持Robin Lovell-Badge评价,“不能被称为是一项‘突破性’的研究,但它必将载入史册。”
多位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专家分析,虽然目前很难证实这项研究的真实性,但是从11月28日贺建奎发表的公开演讲来看,他没有理由说谎。他们都希望贺建奎和相关调查机构能够公开更多的相关资料。
这项实验是,以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敲除体外受精卵中的CCR5基因,从而使婴儿自然免疫艾滋病病毒(HIV)。
由于伦理问题及技术不够完善,基因编辑技术CRISPR-Cas9用于人类生殖细胞是科学界的禁区,在各国都有一条不可随意逾越的伦理红线。当听闻基因编辑婴儿诞生,科普作家、生物化学博士方舟子称,“关键是一开始就错了”。
公众对人类基因编辑的伦理、安全担忧,很快占了上风。科学界最关心的莫过于,谁给了研究者这一权利,如何防范类似研究冒险行为再现?
根据此前的科研规范,能够将这样一项研究应用到人体,最关键的步骤在于伦理审查。
《财经》记者查询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注册号为ChiCTR1800019378的试验,名为“HIV免疫基因CCR5胚胎基因编辑安全性和有效性评估”,研究负责人正是贺建奎。按注册信息,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伦理委员会已经在2017年3月7日批准了这项研究;该医院也是这场试验的主办单位,以及研究实施地点。
11月27日下午,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发布紧急声明,该院伦理委员会的文件上,签名有伪造嫌疑,目前已申请公安机关介入调查。该医院所属的和美医疗集团,成立了调查小组配合卫生监管部门调查。
对伦理这关如何通过、为何不在实验开始前即申报中国监管机构,贺建奎只宣称,其与一些美国顶级的伦理学者,包括斯坦福、哈佛大学的学者探讨过伦理问题,也向很多科学家展示了试验数据。目前,上述两高校未称展开调查;但据CNN报道,贺建奎母校美国莱斯大学的教授Michael Deem已被卷入此事,该人士曾担任过贺三年半的顾问,学校正在调查中。
贺建奎所在的南科大实验室英文官网上,公开了这场基因编辑婴儿的受试者知情同意书。贺建奎在上述人类基因组编辑峰会上,描述了受试者知情同意的过程:第一次是非正式的,一位课题组成员与受试者沟通了两个小时;一个月后,受试者来到深圳,另一名教授接手,继续第二次的知情同意过程,且贺亲自参与。贺说受试者在这个过程中可以随时提问,结束后受试者夫妇也可以私下再讨论。
这份知情同意书告知了研究的主要风险是,如果未击中预期靶点,可能会导致误中的基因产生突变。贺建奎团队的解决方案是,通过全基因组测序、羊膜穿刺术,以及胚胎移植后不同妊娠阶段母亲的外周血检测,使实质性损伤的可能性“降至最低”。该项目团队不承担超出目标的风险,“这超出了现有医学科学和技术的风险后果”。
“真的感觉这个太冒进了。”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朱桢告诉《财经》记者,这次科研完全可以用其他灵长类动物,作为抗艾滋病动物模型。此次人体实验可以说从实验设计和科学目标上,追求的即是新闻性,而不是实验总体的完整性;突破的不是科学前沿,而是伦理学的底线,造成人们对生物技术的恐惧和抵制。
这份知情同意书上,并未说明的事实是,为了避免这对夫妇的孩子感染HIV,编辑基因是否是唯一的选择。一位生物界人士认为,尽管该研究中基因编辑技术比三年前更安全一些,但还要看具体的方案;另外,这次研究选择的基因及病种也不是最后及最佳选择,编辑CCR5基因,并不能完全阻止HlV感染。更何况对艾滋病,现有的知识和技术已能做到可防可控可治。
即便有一份知情同意书,并且提出受试者招募的具体要求(父亲感染艾滋病而母亲不是),也不意味着这项研究合规。北京协和医学院人文学院教授张新庆对《财经》记者说,这些资料需要拿到伦理委员会去审查,如获批才能开展临床研究;如果伦理委员会认为实验风险大于收益,则无法开展。
缺失的伦理审查主体,未辨真伪的伦理审查委员会签名,显示出这项人类试验惊人的草率。
“我不反对通过基因工程的方法去除或修改胚胎的致病基因,但是他们修改的是绝大多数人都有的一个具有重要生理功能的正常基因,这是非常荒唐、违反伦理的。不能因为一个正常基因的产物是病原体攻击的靶点就要把它改掉,否则可以改的正常基因太多了,何况是有重要功能的基因。岂能为了预防艾滋病这种小概率事件,就让婴儿天生失去一项正常生理功能?”方舟子告诉《财经》记者。
一位认识贺建奎的生物科技领域专家以“操之过急”评价这次研究。其实,对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技术跃跃欲试的科学团队并不仅此一家。在2015年初,中国一个科学团队率先使用CRISPR-Cas9对人类不能正常发育到期受精卵进行基因编辑,刺激了许多科学家和组织出面澄清对使用编辑方法的立场。
国际上初步确立基因编辑的伦理红线,标志是在2015年12月的人类基因编辑国际峰会中,来自世界各国的科学家们在华盛顿发表声明,明确划出了一道不得逾越的“红线”:禁止出于生殖目的而使用基因编辑技术改变人类胚胎或生殖细胞。
2017年8月3日,美国人类遗传学杂志联合具有遗传学专业知识的11个团体和国际组织发表了一个联合立场声明,阐述了人类生殖系细胞基因编辑问题的三个关键立场:第一,目前,以怀孕为目的进行生殖系细胞基因编辑是不合适的;第二,当下只要有效监督并得到捐助者的知情同意,没有理由禁止人类胚胎和配子的体外生殖系细胞基因编辑,也不应该禁止公共资金对此类研究项目资助;第三,人类生殖系细胞基因编辑的未来临床应用不应该进行,除非存在令人信服的医学理由、支持其应用于临床的证据基础、道德上的理由,以及公开透明的程序征得利益攸关方的意见。
从这些声明中可见,在体外做生殖细胞基因编辑试验可以,但尚不可以植入人体。贺建奎自称,在三年前就开始基因编辑婴儿研究,一些基因检测费用来自南方科技大学的初创资金。
除了伦理禁区,“技术上的安全性问题还没有充分解决”。中国科学院干细胞与生殖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王宇对《财经》记者称,比如脱靶性问题,这个工作打靶了CCR5基因,但是有可能会打偏,干扰到其他基因,而这会带来无法确定的后果。
贺建奎自述也曾考虑过这项技术的安全问题。但不知为何,很快便放下担忧着手去做了,这也被科学界批评为其前后言行不一致。2017年2月,贺建奎在科学网曾就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撰文称:“不论是从科学还是社会伦理的角度考虑,没有解决这些重要的安全问题之前,任何执行生殖系细胞编辑或制造基因编辑的人类的行为是极其不负责任的。”
朱桢称,之前有研究,CCR5基因突变的人,对于西尼罗河病毒以及流感病毒的抵抗力或显著下降。这不是治疗免疫疾病,而是从一开始就改变了人的基因,让人一辈子暴露在另外一些危险而常见的病毒风险之下,“想想太可怕了”。
贺建奎冒进的后果,可能会对基因编辑领域造成巨大伤害,让这个本来很有前景,甚至改变世界的新技术遭遇不必要的挫折,尤其是对于公众,相关恐惧和不信任会大增。
“过去几天我们学到最重要的一课是,所有的科学研究都必须在公开透明的情况下进行。任何研究,尤其是前沿科学,都不应该以这样一种意外的方式公开,必须经过注册并走完公开程序。”哥本哈根大学人类学教授Ayo Wahlberg告诉《财经》记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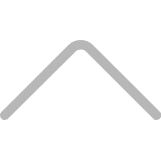
发表评论 取消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