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yce Olson是英特尔的一名员工,几年前,非常突然的,Bryce被诊断出了IV期前列腺癌,肿瘤的侵袭性很强,而且已经发生了多处转移。一开始,Bryce尝试了手术、化疗和放疗,然而这些传统疗法都不能阻止肿瘤的发展。Bryce想,按照这样发展,自己大概看不到女儿小学毕业了。
Bryce Olson讲述自己的抗癌经历
传统疗法的大门虽然被封了,好在,二代基因测序(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NGS)为他打开了一扇窗,美国FDA批准的肿瘤伴随诊断工具FoundationOneCDx(F1 CDx)检测的结果表明,Bryce有可以被靶向的基因突变,根据这个结果,他加入了一个靶向药物的I期临床试验,这让他平安地度过了2年的时间。
基因组变异检测方法的“乱斗”
能和侵袭性非常强的癌症搏斗多年,新癌症疗法(靶向和免疫治疗)和基因测序的快速发展可以说是功不可没。
在靶向治疗领域,目前,已经有数十种药物问世,它们靶向不同的基因组变异,包括点突变(碱基替换、插入或缺失),拷贝数变异以及DNA重排,检测出这些变异是进行靶向治疗的第一步,也是靶向治疗的基础。
那么问题来了,如何检测变异呢?
其实方法很多,传统方法包括扩增阻碍突变系统(ARMS)、荧光原位杂交(FISH)、免疫组化(IHC)和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T-PCR)。虽然是“老资格”,技术成熟,但是这些方法都各有利弊。例如,ARMS检测的敏感性很高,但它仅能用于检测已知的碱基替换、插入或缺失。FISH和IHC均可以用于检测DNA重排、扩增和融合突变,但难以对融合突变进行区分[1]。这就意味着,在实际应用中,只使用单一的检测方法可能会导致患者的变异无法被检测到。
事实也确实如此,根据一些临床试验的数据,在肺癌中,有大约35%的ALK基因重排无法通过FISH检测到,而在乳腺癌中,有大约15%的HER2扩增无法通过FISH和IHC检测到。
随着NGS与临床的结合,似乎又给科学家、肿瘤临床医生与病人带来了抗击癌症新的武器。NGS可以一次性的对所有基因或是特定基因进行检测,这是上述的传统方法无法在单次检测中完成的。
不过NGS只是一个技术,如何利用它为癌症患者服务呢?一般情况下,根据不同的癌种,患者可以接受特定的几个或几十个基因的测序。以非小细胞肺癌为例,检测的基因通常包括EGFR、ALK和ROS1,根据突变的类型不同也有不同的靶向药物使用。
除了这三个基因外,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也可以对BRAF、MET、HER2、KRAS和RET这几个基因进行检测。
但此前最经济实用的做法基本上是集中在“热点序列”上,对这些特定的基因变异进行检测。这就如同雪夜的路灯一样,我们只能看到灯光下过往的汽车,而灯光以外的世界有什么?一片漆黑。其结果显而易见,这样的检测会让一些患者会出现“假阴性”。
在2016年的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对250例EGFR外显子19缺失突变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肿瘤样本进行了全面基因组测序(CGP),发现有71例患者有可靶向的缺失突变,但是这其中有12例在之前的诊断中为阴性[2],也就是说,有17%的患者的EGFR外显子19的缺失突变被遗漏了!
如果没有CGP的话,那么这些患者的恐怕就没有机会接受EGFR酪氨酸激酶抑制剂(EGFR TKI)的治疗了。
全面基因组测序与抗肿瘤新时代的左膀——靶向治疗
说起CGP,那就不得不提2017年获得FDA上市批准的F1 CDx,它是首个获批的可以应用于多种实体瘤伴随诊断的CGP产品。F1 CDx是由一家美国的初创企业Foundation One研发的产品,这家公司在起步阶段获得了大名鼎鼎的乔布斯,盖茨基金会,以及谷歌的投资,最近又为肿瘤领域的巨搫瑞士罗氏集团收归旗下。
与普通的CGP不同的是,F1 CDx完全聚焦在目前已知的与肿瘤相关的基因上,获批时,F1 CDx检测的肿瘤驱动基因数目为324个。这与人类的所有的基因相比虽然沧海一粟,但优势也是十分明显:第一,与全外显子组测序相比,经济实惠;第二,检测效率高;第三,检测结果可以直接运用到肿瘤临床治疗中。
F1 CDx的测序结果是一份详尽的报告,并会发送给医学专家进行分析,根据可靶向的靶点为患者提供已经获批的药物治疗方案,以及目前FDA已经批准的临床试验中患者有机会可以参加的临床试验,就像开头提到的Bryce一样。
给大家举个栗子,在巴西圣保罗,一名51岁的男子在肠镜检查中发现了直肠恶性肿瘤,而且已经转移到了肝 脏和肺部,在直肠切除和化疗后,患者的病情得到了部分缓解,接着,他又通过手术切除了转移的肿瘤。然而,5个月后,在他的肝 脏和肺部,医生发现了新的肿瘤灶以及脑和多个淋巴结的转移。
为了控制病情,他又接受了放疗和两次手术,术后继续用化疗和抑制肿瘤血管生成的贝伐单抗进行治疗,这一次,病情的稳定维持了6个月。6个月之后,肿瘤再次来袭,此时,这名男子已经出现了恶病质和肝性脑病,束手无策的医生这时候想到了F1 CDx。通过F1 CDx测序后,医生找到了6种基因变异,其中包括FLT3的扩增,它是急性髓系白血病中最为常见的突变。
基于这个靶点,这名男子开始服用索拉非尼,在治疗后7天内,他的肝性脑病迅速改善。30天后,总胆红素水平从11mg/dl降至正常水平。不过可惜的是,4个月后,他的肿瘤再次出现进展,很快就因为直肠癌导致的肝功能不全而去世了[3]。如果能够更早期进行F1 CDx的检测,这名男子的结局可能会完全不同。
抗肿瘤新时代的右臂——免疫治疗
除了324个肿瘤驱动基因外,F1 CDx获批上市的时候还“夹带”了2个可以预测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疗效的分子标记:微卫星不稳定(MSI)和肿瘤突变负担(TMB)。
为什么说这两个分子标记非常重要呢?这就要从现在最热门的肿瘤免疫治疗说起了。无论是O药,K药,还是T药,虽然针对特定人群的疾病缓解都比过去有显着提高,但在总体人群中的响应率仍然只有20%到30%。面对如此昂贵的药物,患者如何知道自己的肿瘤是否能够对它有响应呢?
这时候就需要“求助”MSI或者是TMB了。首先来说MSI,在细胞中,DNA错配修复路径缺陷(dMMR)会导致基因组不稳定,致使突变积累或出现MSI。从2013年开始,就有研究人员发现,PD-1抗体对携带dMMR的癌症患者可能更有效[4],后来的临床试验也证明了这一点[5],dMMR成为了PD-1抗体疗效预测的指标。
但是,dMMR在不同癌种中携带者的比例大不相同,且大部分癌种中比例都不高。所以,想要更多的患者能够获益,还需要其他更有代表性的标志物,于是,TMB出现了。从这个名字中我们也能猜到,TMB越高,患者或许就能从免疫治疗中获益越多。
2015年和2016年,两项临床研究验证了这个观点[6,7],奠定了TMB在预测免疫治疗效果中的地位。基于这些研究成果,今年,TMB被写入了非小细胞肺癌的NCCN指南中,作为衡量患者是否可以接受免疫治疗的推荐检测方法,另外,使用经过验证的NGS panel检测MSI/dMMR以及其他几个常见基因变异也被更新进了NCCN指南。
不过,检测TMB所用的全外显子组测序技术成本可是相当之高,这完全限制了TMB在实际临床中的应用。
F1 CDx恰好解决了这个问题,它分析数百个癌症相关基因的总计约1.1Mb大小的外显子序列,然后计算TMB水平,多个研究表明,它的一致性高[8-10],与全外显子组测序一样准确[11]。当然,成本可比全外显子组测序要低多了。
助攻抗肿瘤新希望的诞生
除了帮助患者发现治疗靶点,链接到治疗方案外,基因测序技术在新药的研发和药物适应症的扩大研究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几年前,美国范德比尔特大学医学中心接收了一名患有IV期肺癌的33岁男性,他没有任何已知的可以被靶向的基因变异,然而,F1 CDx的检测结果显示,这名患者具有EGFR激酶结构域重复(EGFR-KDD),这种变异还从来没有在肺癌中被发现过。体外培养的细胞实验表明,EGFR-KDD确实是一种驱动肿瘤生长的变异,在几种EGFR TKI中,阿法替尼抑制癌细胞生长的效果最为明显。
由于患者已经对标准的一线化疗出现抵抗了,研究人员只能尝试使用阿法替尼对他进行治疗。很快,患者的病情就得到了缓解,2个周期的治疗后,肿瘤缩小了约50%!然而不幸的是,7个周期的治疗后,患者对阿法替尼产生了耐药[12],但却给EGFR肺癌药物的研发打开了一个新思路。
患者在阿法替尼使用前(左)、使用2个周期(中)和使用7个周期(右)后的肿瘤(红色箭头所指)直径(cm)变化:6.62 vs. 2.72 vs. 6.20
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关注到前些天被刷屏的“有效率75%的重磅神药Larotrectinib”,当然了,这个“有效率75%”是个错误解读,应该是“在临床试验中,患者的总体缓解率(ORR)为75%”。Larotrectinib是一款广谱抗癌药物,靶向NTRK基因融合,覆盖17种癌症,但实际上,NTRK基因融合是一种非常罕见的基因突变,在美国,预计只有2500-3000名患者[13],在中国,它的突变率大约为0.3%[14],按这个比例,患者也只有30000人左右。
虽然适用人群窄,但是NTRK基因融合是最早被鉴定出来的肿瘤驱动基因之一,目前,只有基于NGS的检测方法才能高敏感性和高特异性的检测出NTRK基因融合,传统方法中,IHC和RT-PCR对此完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FISH倒是可以,但因为NTRK家族包含3个基因[15],所以它需要进行多次检测,而且还要求高度专业化的病理学分析才可以[16-19]。
如果无法准确地检测出突变的话,那么临床试验的进行毫无疑问会受到阻碍,更不用说正式上市,真正的应用到大多数患者中了。
除了Larotrectinib外,针对NTRK基因融合,罗氏也联合Foudnation Medicine正在开展一项临床研究,不过不同的是,Entrectinib不但针对跨肿瘤的NTRK基因融合的患者,还同时针对ROS1基因融合,今年10月ESMO期间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包括至少19种病理学肿瘤类型(按肿瘤部位的常规分类是10种类型)对Entrectinib治疗有应答[20]。
不同类型的癌症患者肿瘤长径总和(SLD)的最优变化(%)
Entrectinib的“广谱”抗癌特性有可能重新定义癌症患者个体化治疗,已被美国FDA授予突破性疗法(BTD)认定。与此同时,NGS也被视为患者接受不定型肿瘤(tumor agnostic)治疗的必要条件。
有能够被靶向的靶点和检测方法,才会有新药物的成功研发和上市,这一点,也是正在经历癌症复发的Bryce的愿景,是的,在平安度过了2年后,Bryce对服用的靶向药物耐药了,检查结果显示,他的肿瘤又开始闻风而动了。
而Bryce依然没有放弃,他寻求到了Broad研究所和其他一些癌症研究领域研究人员的合作,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在大量的基因测序数据中进行筛选和分析,希望能够从中发现新的靶点和药物。
现在一边工作一边积极治疗的Bryce还积极参加到患者倡导运动中来,无论到哪里,他总会穿着一件黑色T恤,上面印有两个英文单词:“Sequencing Me”,NGS将他从死神的手上夺了回来,他希望所有的癌症患者都明白,在今天这个时代,接受NGS不应该是只属于少数患者的奢侈品,而是一件必需品。他也渴望自己和向他一样的数百万患者能够受益于NGS以及随之而来的新的治疗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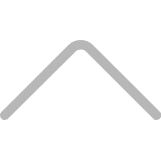
发表评论 取消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