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年前,我妹妹在她的脖子和手臂上发现了肿块,并被诊断出患有癌症。从那天起,她开始受益于科学对癌症的理解。每当她去看医生时,他们都会测量特定的分子,这些分子可以提供该如何做以及下一步该做什么的信息。每隔几年就有新的医疗选择。每个人都知道她因癌症而英勇地抗争。今年春天,她在一项临床试验中获得了创新的新药物治疗。它戏剧性地击退了她的癌症。猜猜我将在这个感恩节上和谁度过?我活泼的妹妹,她比我有更多的运动,和这个房间里的许多人一样,过去时代越来越多地谈论致命的疾病。在我们有生之年,甚至在十年之内,科学将可以改变某些疾病的意义。
但不适合所有疾病。我的朋友罗伯特和我是研究生院的同学。罗伯特很聪明,但每过一个月,他的想法似乎变得更加混乱。他辍学了,在一家商店找到了工作......但情况也变得复杂。罗伯特变得害怕并且胆小。一年半之后,他开始听到声音并认为有人正在追他。医生诊断他患有精神分裂症,他们给了他开了最好的药物。那种药物使声音更安静,但它并没有恢复他聪明的头脑或他的社交联系。罗伯特努力与学校,工作和朋友的世界保持联系。但他还是远离了,今天我不知道在哪里找到他。如果他看这个,我希望他能找到我。
为什么医学为我的妹妹提供了这么多,而为罗伯特这样的数百万人提供的帮助却少得多?需求就在那里。世界卫生组织估计精神分裂症、双相情感障碍和严重抑郁症等脑部疾病是世界上生活和工作能力长年丧失的最大原因。部分因为这些疾病经常在生命的早期发生,在许多时候,在年富力强的时期,比如人们正在接受教育,开始职业生涯,建立关系和家庭一样。这些疾病可能导致自杀;它们经常会妨碍一个人充分发挥潜能的能力;它们是造成这么多悲剧的原因:失去了人际关系和联系,错失了追求梦想和想法的机会。这些疾病以我们根本无法衡量的方式限制了人类的可能性。
我们生活在一个在许多其他方面都有深刻医学进步的时代。我妹妹的癌症故事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同样的还有心脏病。他汀类药物可以预防数百万次心脏病发作和中风。这些深刻的医学进步的领域有一个共同点:科学家发现了对疾病很重要的分子,他们开发了检测和测量体内分子的方法,并且开发了对这些分子进行干扰的方法——其他分子(药物)。这种策略一次又一次的奏效。但是当谈到大脑时,这种策略是有限的,因为今天,我们还不知道大脑是如何运作的。我们需要了解对每种疾病重要的那些细胞,以及对于每种疾病,这些细胞中的哪些分子很重要。这就是我今天要谈论的事情。
我的实验室开发了一些技术,我们试图将大脑变成一个大数据问题。你看,在我成为一名生物学家之前,我从事计算机和数学工作,并且学到了这一课:无论你从哪里收集到大量的、关于系统功能的正确数据,你都可以通过强有力的新方法来使用计算机了解该系统及其工作原理。今天,大数据方法正在改变我们经济中越来越大的领域,它可以在生物学和医学方面做同样的事情。但是你必须拥有正确的数据类型。你必须有关于正确事物的数据。而这通常需要新的技术和想法。这就是我实验室中科学家的任务。
今天,我想告诉你我们工作中的两个故事。我们在试图将大脑变成大数据问题时面临的一个基本障碍是,我们的大脑由数十亿个细胞组成。我们的细胞不是通才;它们是专家。与人类一样,它们专注于成千上万种不同的细胞职业或细胞类型。
事实上,我们身体中的每种细胞类型都可能发表一个生动的TED演讲,谈论它在工作中的作用。但作为科学家,我们今天甚至不知道有多少细胞类型,我们不知道这些演讲的标题是什么。现在,我们知道关于细胞类型的许多重要事实。它们的大小和形状可能有很大差异。一个细胞会对另一个细胞没有反应的分子做出反应,它们会制造不同的分子。但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点对点的方式获得这些见解,一次一种细胞类型,一次一种分子。我们希望能够快速,系统地学习所有这些细胞。
现在,直到最近,如果你想要清除大脑或任何器官中的所有分子,你必须先将它打碎成一种细胞状冰沙。但这是一个问题。一旦你对细胞进行了研究,你就只能研究细胞的平均状况,而不是单个细胞。想象一下,如果你试图了解像纽约这样的大城市是如何运作的,但你只能通过回顾一些关于纽约普通居民的统计数据来做到这一点。当然,你不会学到很多东西,因为所有有趣、重要和令人兴奋的东西都在于多样性和专业化。我们的细胞也是如此。我们希望能够研究大脑,不是像细胞冰沙,而是像细胞水果沙拉,在其中可以生成关于每个单独水果的数据并从中学习。
所以我们开发了一种技术来做到这一点。你将要看的一个视频。在这里,我们将数以万计的单个细胞包装成自己的微小水滴,用于自己的分子分析。当一个细胞落在一个小滴中时,它会遇到一个微小的珠子,这个珠子可以提供数百万个DNA条形码分子。并且每个珠子向不同的细胞提供不同的条形码序列。我们将DNA条形码整合到每个细胞的RNA分子中。这些是特定基因的分子转录版本。然后我们对数十亿个这些组合分子进行测序,并使用这些序列告诉我们每个分子来自哪个细胞和哪个基因。
我们将这种方法称为“Drop-seq”,因为我们使用液滴分离细胞进行分析,我们使用DNA序列进行标记和清点并跟踪所有内容。而现在,每当我们进行实验时,我们都会分析数以万计的单个细胞。今天,在这个科学领域,挑战越来越多,如何尽可能快地从这些庞大的数据集中学习?
当我们开发Drop-seq时,人们常常告诉我们,“哦,这将使你们成为每个主要大脑项目的首选参考。”那不是我们看到它的方式。当每个人都贡献大量令人兴奋的数据时,科学才是最好的。所以我们写了一本25页的教学书,任何科学家都可以从头开始构建自己的Drop-seq系统。在过去两年中,该指导手册已从我们的实验室网站被下载了50,000次。我们编写的软件可供任何科学家用来分析Drop-seq实验中的数据,该软件也是免费的,并且在过去两年中已经从我们的网站被下载了30,000次。数以百计的实验室向我们描述了他们使用这种方法所做的发现。今天,这项技术被用于制作人体细胞图谱。它将是人体中所有细胞类型的图谱,以及每种细胞类型的特定基因图谱。
现在我想告诉你,我们试图将大脑变成大数据问题时面临的第二个挑战。而这个挑战是我们想要从成千上万的活人的大脑中学习。但是,在人们活着的时候,无法进入他们的大脑。但是,如果我们不能接触这些分子,我们怎么能发现分子特征呢?答案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即信息最丰富的分子是被我们的DNA编码的蛋白质,DNA包含我们的细胞用来制造所有蛋白质的配方。并且这些配方因人而异,导致蛋白质的精确序列,以及每种细胞中每种蛋白类型的含量都在人与人之间产生差异。它全部编码在我们的DNA中,它都是遗传学,但它不是我们在学校学到的遗传学。
你还记得大B,小b吗?如果你继承了大B,你会变成棕色眼睛吗?这很简单。很少有这么简单的特质。甚至眼睛的颜色也不仅仅是单一的颜色分子。像我们大脑的功能那样复杂的东西是由数千个基因的相互作用所造成的。并且每一个基因在人与人之间都发生有意义地变化,我们每个人都是变异的独特组合。这是一个巨大的数据机会。而今天,越来越有可能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取得进展。人们以创纪录的数量为基因研究做出贡献,世界各地的科学家正在彼此分享数据,以加快进展。
我想告诉你一个我们最近在精神分裂症遗传学方面的一个发现。因为来自30个国家的50,000人将DNA用于精神分裂症的基因研究,这件事才成为可能。多年来人们已经知道,人类基因组对精神分裂症风险的最大影响来自编码我们免疫系统中许多分子的基因组的一部分。但尚不清楚具体是哪个基因负责。我们实验室的一位科学家开发了一种用计算机分析DNA的新方法,他发现了一些非常令人惊奇的东西。他发现了一种叫做“补体成分4”的基因-简称为“C4”——在不同人的基因组中有几十种不同的形式,这些不同的形式在我们的大脑中产生不同量的C4蛋白。他发现我们的基因产生的C4蛋白越多,我们患精神分裂症的风险就越大。
现在,C4仍然只是复杂系统中的一个风险因素。这不是大B,但它是关于重要分子的见解。长期以来,像C4一样的补体蛋白在免疫系统中的作用是众所周知的,它们作为一种分子标签写着“吃我”。标签贴在我们体内的大量碎片和死细胞上,并邀请免疫细胞消除它们。但是我的两位同事发现,C4标签还可以放在大脑的突触上,使它们消失。现在,突触的产生和消除是人类发展和学习的正常部分。我们的大脑一直在创造和消除突触。但是我们的遗传结果表明,在精神分裂症中,消除过程可能会进入超速状态。
许多医药公司的科学家告诉我,他们对这一发现感到兴奋,因为他们多年来一直在免疫系统中研究补体蛋白,已经学到了很多关于它们如何发挥作用的知识。他们甚至开发了干扰补体蛋白的分子,已经开始在大脑和免疫系统中测试它们。它是一种可能解决根本原因而不是个体症状的药物通路,我们非常希望许多科学家的这项长期工作能够取得成功。
但C4只是数据驱动的科学方法在数百年悠久的医学问题上开辟新潜力的一个例子。我们的基因组中有数百个基因可以导致脑部疾病的风险,其中任何一个基因都可能指引我们发现下一个重要的药物分子。并且有数百种细胞类型含有不同的基因组合。当我们和其他科学家努力生成数据,并从这些数据中学习我们所能做的一切时,我们希望开辟更多的新战线。遗传学和单细胞分析只是试图将大脑变成大数据问题的两种方法。
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们实验室的科学家正在创建一种技术,用于快速绘制大脑中的突触连接,以确定哪些神经元之间正在进行对话,以及这种对话在整个生命过程中和疾病期间的变化。我们正在开发一种方法,在一个单独的试管中测试具有数百个不同人类基因组的细胞对同一刺激的反应。这些项目汇集了具有不同教育背景和兴趣的人才——生物学,计算机,化学,数学,统计学,工程学。但是,科学的可能性将不同兴趣的人们团结在一起。
我们希望创造的未来是什么?想想癌症。我们已经从一开始对癌症起因的无知(癌症通常归因于个人心理特征),发展到对癌症真正生物学原因的现代分子学理解。这种理解在今天导致了一个个创新医学发现,尽管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我们周围已经有很多被治愈的、在几十年前被认为是无法治愈的癌症患者。像我妹妹这样的数百万癌症幸存者发现自己还可能活很多年,拥有新的工作,快乐和人际关系的机会。这就是我们希望在精神疾病领域创造的未来——一种真正的理解,同情和无限的可能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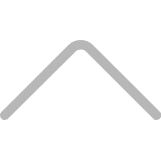
发表评论 取消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