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制定者正对特效药的高价进行前所未有的审查。吉利德公司(Gilead)一个疗程高达84,000美元的丙肝特效药Sovaldi就是导致这种情况的“罪魁祸首”(或者说是“功臣”)之一,而除此之外还有福泰制药(Vertex)的Kalydeco、默克公司(Merck)的Keytruda,以及其他一系列价格高达六位数的药品。
制药行业的回应正如我们所料。他们解释说,为了给创新之火提供燃料,高药价是必要的。的确,如果没有潜在的回报,投资者当然会敬而远之。不过,后面的问题要如何解答呢?——药价到底需要定多高呢?什么时候高药价的逐利成分会超过推动创新的需要,并败坏市场呢?
我觉得我们已经走到了这一步。举个确切的例子:对于由一种后天基因异常——名为ALK(间变性淋巴瘤激酶)基因重排——导致的肺癌(或其他癌症),目前有七种相关治疗药物正处在人体试验阶段(参见图表)。罗氏公司(Roche)的Alectinib处于试验的第三期,Ariad公司、Tesaro公司、辉瑞公司(Pfizer)以及Ignyta公司的药物都在第二期,另外还有四种药物即将进入人体试验阶段。这些药物全以同一种致癌机制为目标,数量不可谓不多。
如果ALK基因重排导致的肺癌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市场,这倒可能说得过去,但事实并非如此。治疗这种肺癌的一线和二线适应症的重点药物已经分别被辉瑞的Xalkori和诺华公司(Novartis)的Zykadia所把持。而且,在转移性肺癌中,只有3%-8%是由ALK基因突变引起的,这相当于美国每年只有区区几千人罹患这种疾病。
如果这不是一个巨大的市场,那么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ALK药物呢?
我认为原因是高药价。联邦医疗保险计划(Federal Medicare)以及大部分私营保险公司必须在处方中包含新的抗癌药物,无论它们的价格几何,或者是否存在比较便宜的替代品。而且,随着制药行业不断尝试开出越来越高的价格,他们除了遭遇一些言辞犀利的社论以及关于病人因病致贫的报道以外,一切都进行得顺顺当当。
在每一种抗癌新药都标上高价的情况下,制药公司顺着一条很多人已经走过的道路,在逐利的比赛中你追我赶,这使得进行高风险的创新变得不太具有吸引力,而要想获得新药以解决那些未满足的需求,高风险创新仍是唯一的道路。此类新药的产生所需依赖的机制在今天仍然只是一种设想。
你可能会说,这不是非此即彼的问题。但如果是那样,那我们关于为什么需要高药价来推动创新的整个讨论就会分崩离析。显而易见,投资研发新药的资金只有这么多,如果那些钱被用于研制另一种治疗ALK基因重排疾病的药物,那么就没有钱被用于研制基于未经证实思路的新药。科研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这些研究对患者的招募工作也同样如此。

一些宏观事件展示了高药价所产生的扭曲效应。吉利德公司以89%的高溢价率收购了Pharmasset公司,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可以在任何有疗效的抗丙肝药物上面贴上一个闻所未闻的价签。
这笔收购交易为吉利德公司带来了惊人的利润,这就是我们常有耳闻的投资者回报。但是,且慢,这并非天价Sovaldi推动抗丙肝药物创新的故事啊。这个故事说的是,制药公司吉利德意识到了被Pharmasset其他竞价者以及华尔街所忽视的一点,即药价不受地心引力的制约。我们知道,Pharmasset对其抗丙肝药物一个疗程的预期收费是36,000美元——只有吉利德公司Sovaldi价格的42%。所以,这样的定价——这个低得多的定价——才是推动创新所必要的,吉利德公司的价格可不是。
新特效药的惊人高价如今已经在人们意料当中,那些错过Sovaldi的制药公司下一次不会再失手。他们会给自己的药物标上疯狂的价格,而那意味着更高的估值。
罗氏公司刚刚在一笔总值超过80亿美元的交易中,以40%的溢价率收购了Intermune公司。后者研制了一种药物,名为Esbriet。这是一种了不起的药物,可能惠及10万遭受特发性肺间质纤维化之苦的人群。当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FDA)审批通过Esbriet时,罗氏公司宣布一年治疗费用为94,000美元,是该药在欧洲市场标价的两倍还多。这是很简单的算术题:如果他们能够实现完全的市场渗透,罗氏公司将能在一年当中收回全部投资。
还是这个道理,给Esbriet贴上高价标签的可能性并没有刺激创新,而是促使罗氏有钱收购Intermune。现在的投资者感到非常高兴(我也为他们高兴),但当初做出研制Esbriet这个高风险决定的时候,他们当中又有多少人在场并掏钱进行了投资呢?
高药价对于推动创新或许是必要的,然而,制药行业虽口口声声说自己是为了让稀有战果的获取成为可能,但市场却告诉了我们一个相反的事实:高昂的药价已经成为了战果本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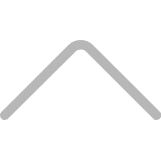
发表评论 取消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