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的头部是背后掌握大数据的企业,而不是只会产药的企业。
1985年,当达拉斯电工Ron Woodroof用啤酒送服下两片AZT(齐多夫定)后,奇迹并没有发生,他体内的HIV病毒仍在蔓延,而且病情更加恶化......这是电影《达拉斯买家俱乐部》中的一个桥段,当时美国没有治疗艾滋病的有效药物,直到1996年,雅培(Abbott)公司经10年研发的抗艾“神药”Ritonavir(利托那韦)上市,大幅提高了艾滋病患者的存活率——两年内,美国HIV相关死亡人数从每年的50000人下降到约18000人。
正当美国患者们在互助会里彼此拥抱鼓励之时,药却出了岔子。
1998年,Ritonavir上市两年后,被发现晶型发生转化,药物性质随即改变,其生物有效性大大降低。雅培不得不召回所有产品、清空生产线,重做晶型研究、制剂开发等一系列工作,前后经济损失超过 2.5 亿美元,雅培成了“哑赔”。
在事后接受FDA(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问责时,雅培的首席科学官硬着头皮挤出了一句真心话:“药物的多晶型现象就像自然界的龙卷风一样,是不可预测的状况。”
“龙卷风般不可预测”,这就是制药行业面临的长期困境:它由生物学假说驱动、以试错为主,效率低下。这直接导致制药行业具有投入高、风险高、周期长、门槛高的特点。
但现在,改变正在悄悄发生。
从2014年到2017年,中国集中涌现了晶泰科技、零氪科技、寻百会、深度智耀、智药科技等新型医药科技公司,原本高壁垒、格局相对稳定的制药行正迎来变局,以大数据、AI为代表的新兴科技正在着力提升制药环节的效率。
「甲子光年」采访了中国药物研发科技公司、专注生物科技和医疗领域的投资人、药物研究机构等多方角色,以探究这一“变局”背后的深层逻辑、机遇和影响。
我们看到的新局面是:新技术公司各持所长、从不同环节切入,并努力向上下游迫近;研究机构搭建技术平台自组公司;传统药企嗅到风向,谋求合作、收购;投资机构跃跃欲试而又冷静克制。
在大众看不到的研究室、谈判桌上,手握新技术的拓荒者们,正试图在药物研发的不同环节跑马圈地。
便宜不了的药价
上映12天后,《我不是药神》票房突破25亿,整个中国也陷入一场大讨论:为什么药这么贵?
巧合的是,根据以医科闻名的美国塔夫茨大学2016年的数据,新药研发的平均成本也是25亿多——不过是美元。《我不是药神》的电影从剧本到成片花了3年;而药企要做出一款新药,则普遍需要10到15年,而且成功与否还不一定。
根据生物技术创新组织(BIO)的数据,每5000到10000个进入研发管线的候选药物,最终能被FDA批准上市的不到10个。且在10种上市药品中,只有2种取得的收入可以覆盖研发成本。
高投入、高风险、长周期,这直接导致药企研发成本高昂,药价便宜不了。
现行的药物发现流程是这一切的根源。
这套研发流程大致可以分为“药物发现(包括靶点筛选、先导化合物筛选、先导化合物优化)→临床前研究→临床研究(分为I期、II期、III期)→新药申请→批准上市”→药物上市后检测6个阶段。
“药神”电影中治疗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的“格列宁”原型,瑞士诺华制药公司(Novartis)研发的“格列卫”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从1960年发现作用靶点“费城染色体”,到2001年5月被美国FDA批准用于治疗,格列卫的问世跨越了40余年,诺华前后投资超过50亿美金。
仅仅是从发现靶点到找到致癌机理,格列卫的研发团队就花了10年。此后,研发人员还要在成千上万种组合中找到合适的化合物,开展动物实验和I期、II期、III期人体临床试验。每一环都是难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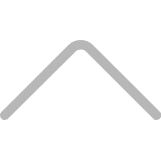
发表评论 取消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