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一些来自制药企业、临床试验机构和地方监管部门的不同声音。他们认为核查工作会给产业带来巨大冲击,通过媒体呼吁“见好就收”,甚至提出中国将“无临床试验可做”。那么,如何理性看待这一争论呢?
药品监管的目标是保障公众用药安全,其包括三个层次逻辑内涵:首先,用药安全的前提是有药可用,药品是企业生产的,产业是监管的基础。其次,有药可用不等于所有人都用得起药,政府要致力于提升民众对药品的可及性。再者,人们在用得起药之后会追求更加安全有效和预防治疗疑难疾病的好药,创新不可或缺。可见,药品监管工作糅合了安全保障、商业发展、科研创新和政治稳定等多重价值,其复杂性不言而喻。
正因此,现代国家的药品监管史,无不充满着公众健康与产业利益的对抗,充满着科学知识与社会焦虑的争锋,充满着创新进步与安全保守的权衡。表面上,反对核查工作是个别企业的抗争,实际上是多重紧张关系的集中爆发。
现实中,药监部门必须权衡公众用药安全的整体利益和临床试验链条中每一个利益相关者的具体利益,后者既反映了企业逐利的天性,又牵涉到地方政府的政绩,还关乎临床试验机构、研究者等切身利益。这就使药监部门难免会“得罪”企业,或是引来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不满。企业深知其诉求一旦被纳入药品安全的政策议程就站不住脚,于是就诉诸大众媒体,将本该是科学命题的药品安全与药物可及性、产业发展等容易形成社会共识的话题混杂在一起,试图用广泛的政策联盟倒逼监管部门让步。
笔者认为,越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监管部门就越需要具备机构自主性,即独立于社会自我决策并有效协调政策执行的能力。换言之,监管部门的角色和作用是在不同价值之间中立、科学地进行抉择,不为企业利益所迫,不为舆论压力所迫,不为地方保护所迫,甚至不为所谓“民意”所迫,而是致力于社会整体与长远利益最大化。
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FDA)在百年发展史中同样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对抗,但强大的机构自主性使FDA始终展露出“捍卫公众健康”的坚定和自信,在挫折中不断壮大并最终成为全球药品监管的标杆机构。
1906年《清洁食品药品法》颁布前,代表食品药品企业利益的美国国会议员以新法案可能阻碍自由贸易为由百般阻挠,不希望监管部门拥有更大权力,因为在一个没有监管的市场上更容易赚钱。企业还通过媒体不断夸大法案的负面效应,希冀煽动民众的反对情绪,当然最终没有得逞。
1937年磺胺酏剂事件导致107人死亡,肇事企业收买了少数医生,试图在社会上造成企业应当免责的舆论声势,但最后还是被处以天价罚金。FDA还借此推动了更为严厉的《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出台。

到了上世纪50年代末,当欧洲的孕妇广泛使用“反应停”减轻妊娠反应痛苦时,FDA以安全性为由对该药物进行了漫长的上市前审批,一些消费者表示强烈不满。但正是这个看似违背“主流民意”的决定,成功避免了“海豹胎儿”悲剧的扩散。
今天美国药监官员可以自信地说:“FDA不是因为永远正确才有权威,而是因为有权威所以永远正确。”
令人遗憾的是,我们似乎在一起又一起公共事件中变得越来越敏感和脆弱,监管部门甚至被舆论牵着鼻子走。典型例证是2013年末的“乙肝疫苗事件”。一些地方媒体接连报道了新生儿接种乙肝疫苗后出现重症和死亡病例,尽管调查表明有关疫苗质量全部合格,死亡病例与接种疫苗无关,但监管部门在应对过程中并未完全占据主动,最后造成一个没有赢家的结局:免疫规划接种率下降,国内疫苗企业遭受重创,政府公信力受损。其教训极为深刻。
要提升我国药品监管机构的自主性,必须兼顾内生动因和外部环境两方面的发展。内部动因包括监管机构的目标、职权和能力,统称为禀赋,核心是有一支懂技术、懂政策、懂沟通的职业监管队伍,并长期稳定下来。外部环境是指监管机构实现自主性的社会网络,由产业、专家、媒体和大众等主体构成。
一方面,监管机构需要尽可能多地嵌入利益相关者的网络当中,以保障监管信息的畅通;另一方面,监管机构与多元主体的联系应尽可能分散,这样才不至于被产业“俘虏”或成为民粹主义的牺牲品。
概言之,拥有多元、分散社会网络的监管部门更容易获得较多的政策支持。随着监管机构实现自主决策和获得广泛支持,其声誉也会水涨船高,进而夯实地位和权威,并最终获得良好的监管绩效。
药品安全一头牵着民心,一头关乎产业,是重大的民生问题、经济问题乃至政治问题。今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获得安全有效药品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在临床试验“核查风暴”的关键时刻,若因为一些杂音而缩手缩脚甚至止步不前,那么最终受损的是每一个国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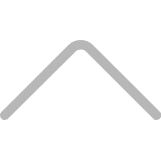
发表评论 取消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