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胞疗法
那还是在1968年,Steven Rosenberg觉得他遇到了一个极其罕见的病例。
Rosenberg当时还是West Roxbury VA Hospital的一名住院医。病人的右上腹疼痛难忍,Rosenberg经过检查之后发现他患有急性胆囊炎。没什么严重的吧,他这样想,进行胆囊切除术就可以了。
但在手术的时候,他发现病人的腹部有一道很长的手术疤痕。Rosenberg问他以前是不是接受过大型手术。“以前得过癌症,”病人淡淡的说:“那还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
Rosenberg调出了他之前的病历,发现他12年前曾因患有消化道癌症在这家医院进行过手术,而且手术时癌症就已经转移到肝 脏上。病历中写道,医生虽然能够将一些大的肿瘤切除,但对小的转移灶却无能为力。当时医生大概是觉得病人的生存期已经不会很长了,因此建议病人出院回家,享受生命的最后时光。
然而让Rosenberg意外的是,当他翻开病历的下一页,他发现这位病人在三个月后再一次来到了这家医院就诊,接下来的一次是六个月之后。病历中写着,一年以后这位病人已经能重返工作岗位了。
Rosenberg觉得他对此只有两种解释。一是医生诊断错误,也就是说这位病人并不是癌症患者,虽然存在这种可能性,但是概率并不高。而第二种可能是病人的癌症经历了自发缓解过程而痊愈了。
但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更低,因为直到Rosenberg遇到这位病人之前,医学文献中仅仅报道过四位这样类型的患者。每年罹患癌症的人何止千千万,能够自发缓解的人,大概只有其中的十万分之一。
Rosenberg检查了病人的原始病理报告以及组织样本,排除了第一种可能。唯一的解释只能是病人经历了自发缓解过程。但在当时来说,这确实算得上是非常罕见的事情了。Rosenberg当时还只是一名住院医,对他来说遇见这样的病人毫无疑问是一种巨大的冲击:这好像是魔法一样,他曾这样说道。
为了让这一魔法能够再次重现,Rosenberg进行了一项听起来很简单的操作。他当时怀疑病人的血液中存在某种能够抵抗癌症的因子,而当时医院恰好还有一位患有相同癌症的病人与那位自发缓解的病人血型相同,因此Rosenberg在征得上级同意之后,将那位病情自发缓解的病人的部分血液输入到了这位患者的体内。
结果可想而知,奇迹并没有发生。接受输血的病人疾病很快进展,不久之后便去世了。尽管没能获得成功,但Rosenberg却变得十分着迷于癌症以及免疫学。为了更加深入地进行研究,Rosenberg暂停了当时的外科手术培训,去哈佛待了一年系统地学习免疫学知识。
Rosenberg出生在一个传统的犹太人移民家庭里。他的父母历经险阻从波兰逃到了纽约,战争结束的时候,Rosenberg父母的大部分亲人早已在大屠杀中丧生。那时的Rosenberg才六岁,一张张的明信片从欧洲寄到纽约,一次又一次地通知他们某位亲人已经在布痕瓦尔德或奥斯维辛的屠杀中丧生。
这大概就是人世间最大的恶了吧。或许是因为太小的年纪就经历过人性的阴暗面,Rosenberg从小就已经很清楚将来要做什么:成为一名医生,拯救患者的性命,而不是去害人。
Rosenberg一直是一个工作狂,在他还年轻的时候,他曾想过跟当时还是女朋友的Alice O’Connell分手,因为他觉得恋爱会分散他进行科研的精力。
“我很喜欢夜晚,”Rosenberg在1992年出版的一本书The Transformed Cell中这样写道。他还能回忆起年轻时深夜在实验室工作的喜悦,喝着在加热器上已经热了几个小时的早已煮的粘稠的咖啡,迎着早晨的太阳走出实验室,大概这世上再找不到能与之媲美的满足感了吧。
Steven Rosenberg
67号病人
Rosenberg刚到NCI的时候,人们对于抗肿瘤免疫反应的了解还极为有限。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纽约的William Coley医生曾使用Coley toxin来激活病人的免疫系统,以此来治疗癌症 (见:肿瘤免疫疗法的诞生)。但由于疗效难以重复,而且制备过程复杂,在化疗以及放射疗法出现之后Coley toxin就逐渐淡出了人们是视野。
其实在Rosenberg刚参加工作的七十年代,依然有很多人不相信人体内的免疫反应能够对抗肿瘤。然而Rosenberg却一直坚信细胞免疫疗法的潜力。那时Rosenberg也做过很多现在看来很蠢的研究,比如将猪的淋巴细胞输入到人的体内。
因为当时已经有研究表明,将某些肿瘤抗原注射到兔子和猪的体内之后能够引发动物的免疫反应。Rosenberg认为既然动物体内能够存在对抗肿瘤细胞抗原的免疫反应,那么动物血液中就有可能存在一些能够对抗肿瘤的物质。但与上一次相同,这一次的尝试依然没有成功。
1976年,Robert Gallo实验室发现IL-2能够刺激T细胞的增殖 (见:抗击艾滋病三十载:挫折、勇敢、坚韧与爱(一))。Rosenberg希望能够将这项发现应用到癌症的治疗上。于是他开始尝试将IL-2加入到小鼠T细胞的培养基中,在五天之后,T细胞数量增长到了之前的30倍。
IL-2是一个极好的研究工具。而Rosenberg当时也恰好需要这一工具,因为他的下一个免疫疗法的方案是提取病人体内的T细胞,然后在体外扩增之后回输到病人体内。
Rosenberg认为,在所有从外周血提取的T细胞中,总有那么几个细胞能够识别肿瘤细胞。如果能够扩增这类细胞的话,将有可能有效的攻击肿瘤细胞。
其实Rosenberg和同事在之前的实验中就证实了,将肿瘤组织与免疫细胞共培养之后再将这些免疫细胞暴露于其他肿瘤组织之后,这些细胞能够在体外杀灭肿瘤细胞。而且他们同时也发现,将IL-2注射至小鼠体内之后能够缩小小鼠的肿瘤。
但是回输使用IL-2培养过的T细胞,以及直接使用IL-2这两种策略都没能取得成功。而且更糟糕的是,Rosenberg发现IL-2的毒性非常大,能够把每位接受治疗的病人送进ICU。
尽管如此Rosenberg依然没有放弃,他开始尝试使用这两种治疗手段的组合方案,也就是向病人体内回输体外培养的T细胞,并同时使用IL-2。
从1980年到1984年,Rosenberg尝试了太多种治疗方法,然而他在之前66位病人身上使用的方案都失败了。但在1984年他遇到了第67位病人Linda Taylor,一位患有黑色素瘤的海军军官。
Taylor是Rosenberg第一位接受这种组合疗法的病人,而她却被成功的治愈了。Taylor到现在依然还活着。Taylor以及其他的一些人的成功治疗,使Rosenberg以及IL-2疗法登上了各大新闻的头条,而他NCI的一些同事也开始称呼他为Stevie Wonder。
之后Rosenberg将数据发表 [1]。但后来人们却发现该疗法的作用其实没那么大,因为该疗法只能够对很少一部分的黑色素瘤以及肾癌患者起效。
在这之后Rosenberg的实验室开始尝试从手术切除的肿瘤中提取其中浸润的淋巴细胞 (这类细胞被称为tumor-infiltrating lymphocytes),并尝试在体外扩增后回输到病人的体内,并同时使用IL-2进行治疗。

而除了疗效的研究,当时Rosenberg实验室还在进行一项TIL的基础研究:提高TIL细胞的体内存活时间,而这个任务也落在了Patrick Hwu的身上。
飞驰的CAR
Patrick Hwu 在1989年加入了Rosenberg的实验室。他当时的第一项工作就是研究TIL细胞的存活时间。为了标记回输至病人体内的T细胞,Hwu将编码新霉素磷酸转移酶的基因导入到了T细胞的基因组。
该基因所表达的酶能够保护T细胞不受新霉素的毒性作用影响。之后将细胞回输至病人或小鼠体内。几周之后再从体内提取T细胞,并向培养基中添加新霉素,之后再检测存活细胞的数量。
Hwu这项研究的结论很让人意外,因为他发现这些回输的T细胞在体内只能存活大约三周的时间。人体内的一些T细胞能够存活长达数年的时间,而这些回输的T细胞却只能存活三周的时间,这大概也能部分解释为何TIL疗法的疗效不佳。
但Hwu和同事认为他们或许能够提高T细胞在体内的生存时间,这一灵感其实来源于骨髓移植。骨髓移植之前通常会使用氟达拉滨/环磷酰胺等清髓化疗方案对病人进行清髓预处理,以摧毁病人的免疫系统。以使之后输入的免疫细胞就能够有足够的生存空间。
虽然这种方式应用于TIL疗法理论上来讲是可行的,但对病人来说也很危险。Hwu的同事基本都是外科医生,只有Hwu一人是之前给病人使用过化疗药物的肿瘤学家。虽然他自己心里也很害怕病人出现问题,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为了提高TIL的疗效他必须进行这种尝试。
但是让他们意外的是,病人对氟达拉滨/环磷酰胺的耐受性并不差。而且他们发现进行清髓化疗之后再使用IL-2会使IL-2的毒性下降,并使部分病人的病情好转。
虽然这种方式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到此时该疗法治疗黑色素瘤之外的其他类型肿瘤的疗效依然非常差。为何这一疗法不能应用于其他类型的肿瘤呢?Hwu决定采用其他手段来解决这一问题,比如将TNF基因导入到TIL细胞中,使这些细胞在迁移至肿瘤位点之后再分泌TNF。
但是这个研究项目进展很缓慢。其实Hwu所进行的这些TIL研究项目的难度都很高,因为Hwu当时发现TIL细胞的体外培养非常困难,而且TIL并不像其他一些类型的细胞那样容易表达外来基因,当时能够提高转染成功率的技术种类也非常有限。
Hwu的这个研究项目最终也没取得成功,但他在TIL培养以及将外源基因导入T细胞的经验,却对Zelig Eshhar当时进行的一项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左:Patrick Hwu 右:Zelig Eshhar
Zelig Eshhar 出生于以色列一个叫Rehovot的小镇。Eshhar的博士以及博士后研究一直专注于免疫学领域的研究。他整天脑子里想的全是免疫,T细胞结构,抗体的功能。而有一天,Eshhar的脑子里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想法:T-body。
Eshhar在研究T细胞受体(T cellreceptor, TCR)的结构的时候,他觉得TCR与抗体的结构和功能存在很多类似的地方。抗体是由B细胞(浆细胞)制造的,而TCR则存在于T细胞上。从结构上讲,TCR由alfa和beta链组成,抗体由重链以及轻链组成,两者都包含恒定区以及可变区。而从功能上讲,TCR以及抗体都有抗原识别的功能。而且表达抗体和TCR的基因属于同一个基因家族。
但TCR与抗体识别抗原的方式存在明显差异,因为抗体能够识别抗原的固有形态,而且具有较高的亲和性,但TCR只能够识别MHC递呈的抗原片段。
如果将TCR的可变区替换为抗体的可变区会产生什么后果呢 (TCR-AntiBODY, T-body)?是否会将抗体的抗原特异性转移到T细胞上呢?
该嵌合结构的抗原受体也同时包含TCR细胞外的恒定区,以及跨膜区和TCR的胞内结构区,因此该受体也应该能够诱导T细胞增殖,介导白介素生成以及使靶细胞裂解。
Eshhar也证实了这一想法的可行性。Eshhar实验室将TNP (2,4,6-三硝基苯) 抗体的可变区移植到了TCR的恒定区上,并证明了该嵌合抗原受体 (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 CAR) 受体具有类似该抗体的特异性,并能够以非MHC限制性的方式结合TNP抗原,并介导白介素生成和靶细胞裂解 [2]。
Eshhar这项研究的目的只是想验证是否能够改变T细胞受体的抗原特异性,并介导其相应的细胞杀伤作用。而将其用于肿瘤治疗领域的设想其实是后来才有的想法。因为当时利用单克隆抗体治疗癌症的研究已经比较多了,而Eshhar的技术理论上能够克服TCR识别肿瘤抗原的缺陷,将TCR的可变区替换为靶向肿瘤抗原的抗体可变区。
而如果将该技术应用于疾病治疗领域的话,Eshhar还需要对以上技术进行改进。因为他之前使用的永生化的细胞或杂交瘤细胞并不能直接应用于疾病的治疗。
但Eshhar在将嵌合基因导入到原代T细胞的过程中却遇到了困难。而Hwu对Eshhar遇到的困难一点也不感到意外,因为淋巴细胞本来就很难表达外源基因,而Hwu之前导入TNF基因的经验却给了他很多经验。
为了能够在原代T细胞中稳定的表达嵌合抗原受体基因,Eshhar决定与Hwu所在的实验室合作。他们使用了来源于抗体的单链抗体片段(single-chain variable fragment, scFv)来解决嵌合抗原表达稳定性的问题。
而先前的实验也证明了scFv与天然Fab片段的结合活性与特异性类似。而且他们使用了Fc受体的γ亚基来转导抗原结合信号,(除此之外,1991年的时候Arthur Weiss实验室证明了包含CD8, and the CD3ζ的CAR也足以激活T细胞)。
Hwu等人构建了作用于三种不同靶标的嵌合抗原受体(chimeric antigenreceptor, CAR),一种是靶向乳腺癌细胞,一种是结肠癌,一种是卵巢癌。然后他们将这些系统导入到靶向黑色素瘤的TIL中。最后他们也证明了来源于MOv18抗体的CAR-T细胞能够有效裂解相应的卵巢癌细胞。
1993年,Hwu以及Eshhar等人将该数据整理成论文发表 [3]。这篇文章也成了CAR-T领域的里程碑式的文章。
但在接下来的十年里,CAR-T疗法却经历了许多的磨难与挫折。
上世纪九十年代,在Rosenberg实验室所在街道的另一侧,位于贝塞斯达的海军医学研究所里,Carl June同样也在研究CAR-T。
(未完待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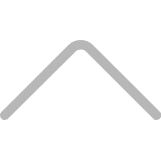
发表评论 取消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