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药方面的投资,在过去5-10年里非常活跃,增长非常快。中国的医药和生物医药行业已经站在世界舞台中大家能看得到的位置,而且变的越来越重要。究其原因,与国家政策变革、人才回归有很大关系。
近期,礼来亚洲基金风险合伙人张志民博士、礼来亚洲基金合伙人林亮、晨兴创投董事总经理黄璐、方恩医药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长张丹博士、通和毓承总裁兼创始管理合伙人陈连勇博士在2018第十届DIA年会上共同探讨了中国生物医药的机遇、变化与挑战。
张志民:当初刚开始进入到中国时,医药投资大概是什么样的?作为投资者,如何选择first in class呢?虽然first in class风险相对比较大,但是回报相对也比较多,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呢?
黄璐:在中国,十几年前还没有first in class,如果真的有,这个first in class药物的靶点在科学上也可能不是特别有效的靶点。
选择投资靶点药物还是要看靶点的生物学本身在科学上是不是被充分验证过?晨兴曾经投过一家做PCSK9靶点的公司,在十三、四年前,PCSK9是一个全新的成药靶点,安进、再生元也刚刚开始着手针对PCSK9的单抗药物研发。虽然在欧洲的一些家族,几代人身上都没有这个基因,他们天生血液里的血脂水平可以低到根本检测不到,但在有该基因的人体上也获得了有效的验证数据。而且有数据表明,他汀类药物在使用到一定的耐受剂量时可以上调PCSK9,对这一靶点做出补充性的验证,靶点本身的风险也就不是那么大了。
如果靶点很新,也未必成功。不一定是靶点不好,有可能是化合物不好。通常用一个新的化合物见证一个新的靶点,不是双重的风险,而是远远高过双重的风险,所以要更加谨慎。
林亮:有一句古诗叫做“两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其实做创新药很像一行白鹭上青天,尤其白鹭当中的第一只,是属于顶着风,往前看很孤独,一只鸟也没有,往后看黑黑的一片,压力很大。
在时间上,目前国内创新药first in class在市场方面的独占期或市场份额都在缩小,从原来六、七十年代的十年独占,到现在的两年,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企业会评判到底要不要做first in class?
如果把过去所做的first in class做系统的数据分析可以发现,在一个创新药成功上市之前,已经有近三分之一的同类研究积累和基础。做first in class的难度是要基于众多优势于一身,而且有很好的运气——不光是自己能成功的运气,还要别人的失败。
做创新药可谓“可遇而不可奢求”,需要有很强的导向,选好靶点后快速跟进,尽量减少时间差距,同时对产品做拓展和挖掘,用更完整的格局来评价。从选择适应症到一线、二线、三线治疗适合不同的病人,以及一些额外疗效、安全性等方面挖掘创新药的价值,才能脱颖而出。就算不能成为first in class,有很好的产品差异化,也会有很好的市场,因此可以用开放的心理去看待创新药到底是first in class还是me better或其他。
张丹:十年前,中国的创新药真的很少,因此这十年的变化尤为巨大。而变化来自于两点:首先是国家推出的人才政策,特别是“千人计划”,为国内带回了一大批成果。粗略统计,国内82个进入临床和注册阶段的创新药,一半来自于“千人计划”人才或者留学回国人员,另一半是国际化公司的项目。第二是中美联合创新,这两年增加的非常快,让人印象非常深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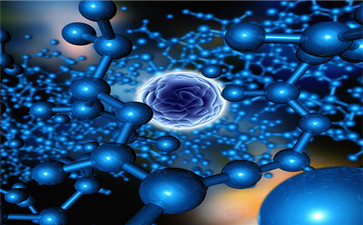
未来,预计还会有更新一波的创新药临床项目要进入中国,原因是中国政策的变化。而且很重要的是,国家刚刚宣布的药品专利链接,有条件的专利数据保护,需要在中国进行临床试验,鼓励了更多的新药研发者早期到中国来。
张志民:去年中国加入ICH,药品政策的变化非常大。做新药受到国家政策的影响巨大,所以在进行新的投资或立项时会有更多考虑。所以针对这些政策变化,当下的投资和立项会有哪些变化呢?对现在的first in class、me too、me better究竟还有多少投资和研发的空间?
陈连勇:对中国来讲,特别确定的一件事是国家的政策还会变,所以投资人需要关注国家政策,但主要还是从临床需求来看项目。
其实临床的需求跟创新药之间的关系不是一个线性关系。我们现在更加关注的不是一个新的靶点,在投资团队的基础上很少有人能够对一个新的靶点有那么好的理解,所以以肿瘤为例,我们会更加关注肿瘤的免疫治疗,给医生提供一个什么样的治疗方案,以及每个病人情况不同时的用药选择。这比发现一个新的靶点容易得多,对临床应用上意义也非常大。
张丹:从做临床的角度来看新靶点或者新的联合治疗的成药性开发,国内有很多优势。第一、国际上通过ICH形成了一个统一的研发市场,我国在加入ICH后风险可以在多市场中承担,即把风险分散在全球,相当于进行了分层处理,实际上非常有助于对新药风险的管控。
另一个特殊的优势是,国内拥有大量优质的、尚未利用的病人资源。他们不在东海岸,也不在高铁线上,而是新农合的病人。无论是进行新药联合治疗,还是做单基因突变等特殊的罕见病研究,这部分病人都是尚未开发的资源。
张志民:如何结合市场和科学来做创新药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课题,从市场的角度来讲,立项很难,而且对于政策的把握也会有很大的影响。以美国销量最高的药物立普妥为例,当时立项时已经是同类药物中的第五个,现在的大公司肯定不可能往前推进的。但该药物上市两年后,就成了best in class。现在虽然专利失效,可是市场仍在。
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免疫治疗最大的案例就是默克keytruda,因为这是一个全新的药物机理,刚发现时谁也看不懂。直到百时美施贵宝同类药物的临床数据出来,keytruda才翻身。现在已经成为默克的“当家花旦”,多种癌症治疗都是keytruda或者它的联合用药。
再比如,孤儿药在二、三十年前的美国也是很难做的,因为市场特别小,但是后来因为美国新政策的影响,十年内孤儿药蓬勃发展。5月22日,我国五个部委也联合公布了第一批罕见病的名单。近期,国家药监局和卫建委也明确孤儿药可以直接利用国外的数据进行申报,与去年12月份时的有条件批准又更往前走了一步,未来国内孤儿药或也将有所期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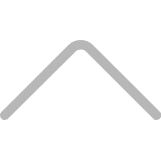
发表评论 取消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