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生化学家Craig Crews首次设法让一种奇怪的新化合物使蛋白质消失时,他把这当作是一种“魔术戏法”,一种“好玩的化学好奇心”。
今天,这种“把戏”正吸引着来自罗氏、辉瑞、默克、诺华和葛兰素史克等公司数十亿美元的投资。“可以推断,几乎每家公司在这个领域都有项目,”安进全球研究高级副总裁及Crews的早期合作者Raymond Deshaies说。
该药物策略称为靶向蛋白质降解,即利用细胞的天然系统来清除不需要或受损的蛋白质。蛋白质降解物有多种类型,而今年正在进行临床试验的类型是Crews在耶鲁大学花了20多年开发出来的——靶向蛋白降解嵌合体(PROTACs)。
大而难处理,PROTACs就药物的定义向传统观念发起挑战,但它们也有可能解决一些不可战胜的疾病。因为它们破坏而不是抑制蛋白质,并且可以与其他药物无法结合的蛋白质进行结合,蛋白质降解剂可被用来追踪药物开发者长期以来认为“无成药性的”的目标:癌症的加剧物如蛋白质MYC,或阿尔茨海默病中的tau蛋白质。
英国邓迪大学生物化学家Alessio Ciulli说,“这是一个新的领域,违反了我们认为有药可靶的规则。”
该领域理应保持乐观。2014年,科学家们发现骨髓瘤治疗药物来那度胺与蛋白质降解剂的作用相似,可以消解两种以前不能消解的蛋白质。然而,并没有缺乏数据来证实PROTAC和其他新兴化合物可以使这些无成药性的蛋白质消失,关于其在体内的作用位置和方式也存在疑问。
目前,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Crews创立的生物技术公司——Arvinas。该公司计划开始针对前列腺癌测试一种PROTAC,攻击其他药物成功靶向的蛋白质。
学术实践
上图中,PROTACs看起来像哑铃,其分子由两个通过一条细绳连接的结合末端组成。在末端起作用时,一个抓住目标蛋白质,另一个锁住泛素连接酶(细胞天然垃圾处理系统的一部分),通过击打一种叫做泛素的小蛋白来标记有缺陷或受损的蛋白质。泛素标签充当“请收集”贴纸,指示细胞中的蛋白质粉碎机(称为蛋白酶体)进行工作。
邻位连接(Proximity)在生物学中有很多,通过简单地将连接酶和靶蛋白结合在一起,PROTAC就可确保目标被标记为破坏。连接酶有效且泛素充足,因此单个PROTAC应该能够在整个细胞中反复执行抓捕和释放功能。
最早关于类似PROTAC分子描述的出版是在1999年,来自马里兰州的一家生物技术公司Proteinix的两位科学家。在专利中,John Kenten和Steven Roberts提出了利用细胞的蛋白质降解系统。对此同事们并不认同,认为同时结合两种蛋白质(不需要的蛋白质和连接酶)会使药物发现变得复杂。
美国的另一边,另一队人也在思考同样的想法。1998年,在华盛顿西北部的研究结束后,Deshaies在Crews的一张海报前停了下来,听他谈论用小分子将两种蛋白质连接到一起。当时的Deshaies是加州理工学院的生物化学家,在泛素连接酶方面有深入研究。人类基因组能编码其中的大约600个,需要与其他蛋白质形成复合物来进行标记。约一年前,Deshaies等人共同发现了一个蛋白质家族,现已知其含有250个泛素连接酶。Deshaies回想道:“如果能将泛素连接酶连接起来,可能就会出现蛋白质的泛素化及其降解。”
Crews当时正在开发一种与PROTACs作用相反的药物,其可阻断细胞中的泛素系统,导致蛋白质处于危险水平,并最终引发细胞死亡。这项研究的结果就是carfilzomib(Kyprolis),现被用于治疗血癌多发性骨髓瘤。Crews说:“我认为反面的研究同样有趣。事实证明确实如此。”
Crews和Deshaies很快发表了一篇研究,证明他们的首个PROTAC(Protac-1)在爪蟾蛙卵提取物中成功地靶向目标并使癌症相关的蛋白(METAP2)出现降解。
Protac-1远远称不上一种药物,Crews称这是一次“学术实践”。
第一代PROTACs依靠大而笨拙的肽链来结合连接酶,在人体细胞中的活性很低,因此必须找到一种方法使该连接酶结合末端更像药物一样。在葛兰素史克的资助和研究支持下,Crews继续推进,主要靶向一种特别的连接酶——VHL综合症抑癌基因。2012年,Crews与他的团队报道了一种用于VHL的小分子黏合剂。Crews终于开始相信PROTACs可以成为药物。
诱捕小分子
Crews并不是唯一一个深究蛋白质降解的人。2010年,波士顿Dana-Farber癌症研究所的化学生物学家James Bradner读了一篇由东京工业大学Hiroshi Handa带领的日本研究小组的论文。Handa一直在研究为什么沙利度胺(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在一些国家被批准用于怀孕期间的恶心)会导致肢体发育出现问题。使用沙利度胺作为诱饵捕获细胞中的蛋白质,Handa研究发现该药可以钩住并阻断一种叫做cereblon的泛素连接酶的活性,这种抑制会影响斑马鱼和小鸡的肢体生长和发育。

Bradner意识到,如果沙利度胺与泛素连接酶结合,或许能找到方法来结合相同的连接酶,但要靶向与疾病有关的蛋白质。2013年,Buckley加入Bradner的团队,他们开始寻找能与cereblon相结合的小分子。
3D structure of PROTAC MZ1 bound to E3 ligase von Hippel-Lindau complex and target Brd4 bromodomain
2015年5月、6月,Bradner、Ciulli和Crews带领的三个小组发表了五篇单独的论文,都是描述PROTACs具有效力且有类似药物活性。与GSK的Ian Churcher一起,Crews将PROTAC与VHL结合,将一些蛋白质的水平降解至低于其在未经处理细胞中的水平的10%。Bradner团队将PROTAC用于降低致癌蛋白的水平,Ciulli团队将VHL作为连接酶来降解相同的蛋白。
除了设计类似药物的蛋白质降解剂,Crews和Bradner的团队各自都建立了系统(分别为HaloPROTACs和dTAG),使研究人员能将靶向的蛋白质降解作为实验室里的一种工具,在培养的细胞以及小鼠中使用基因标记对蛋白质的破坏进行标记。
Bradner于2016年离开了Dana-Farber,成为诺华生物医学研究所的主席,他估计约有30种不同的工具已经吸纳了该技术。他说,“要从这些配体中产生真正意义上的药物,挑战意义重大。”
淘 金 热
2015年小分子PROTACs爆发后,已离开该领域的Deshaies写了一篇评论文章:“PROTACs有可能成为一种主要的新型药物,或许超过有史以来最热门的两个药物开发领域(蛋白激酶抑制剂和单克隆抗体)。淘金热已经上演了!”2017年其加入安进,负责安进该领域的工作。
预计将于2019年中期开始的Arvinas试验包括28-36名转移性前列腺癌男性患者,试验周期为9个月。任何新型药物都会追求生物学和毒理学目标,Arvinas的首个候选药物也不例外。公司希望通过降解而不是抑制该受体,让PROTAC治疗那些已对现有药物产生耐性性或没有从现有药物中受益的患者。
还有一点存在疑问——蛋白质降解剂是否可以在人体中发挥作用。完全组合的PROTAC打破了传统的药物实践经验法则,其中最主要的是大小。好的小分子药物通常小于500 dalton,而目前的PROTACs大小则超1,000 dalton。因此Crews怀疑分子进入细胞是因为它们可能被细胞膜识别为两个碰巧被拴在一起的小分子,而不是一个大分子。
许多难攻克的蛋白质靶标的问题在于,大多数小分子药物或单克隆抗体需要与酶或受体上的活性位点结合才能发挥作用,但人类细胞中80%的蛋白缺乏类似活性位点。然而PROTACs可通过任何角落、裂缝或缝隙抓住蛋白质,不需要活性位置就能发挥作用。
已有一些证据支持该方法。去年,伦敦癌症研究所的一个研究小组研究了一种小分子,不需要活性位点就可与转录调节因子结合。它们通过给泛素连接酶cereblon附着黏合剂产生有效的PROTAC。
但该领域仍缺乏已发表的证据来证实PROTAC可靶向并降解有价值、无成药性的蛋白质。Deshaies说,针对很难结合的一个未命名的高价值癌症靶点,安进的PROTAC在培养的细胞中和动物体内显示都有效。Arvinas在其网站上称,直接注射其tau蛋白质降解剂到小鼠海马后,tau水平降低了50%。
通过开发针对一系列疾病的PROTACs,Taylor表示许多研究者希望证明该技术是“治疗领域不可知论的”。各个团队也在努力扩大连接酶库。目前主要使用的有四种,包括VHL和cereblon,可利用连接酶的广泛性可使药物开发者将最有效的连接酶-PROTAC组合与其细胞类型或目的蛋白质相匹配。
受到新目标、效力的提高和即将开始的临床试验的鼓舞,研究者们已准备好证明蛋白质降解剂不仅仅是一种魔术戏法。Ciulli说,“没有任何限制,只是时间问题。”
点击下图,预登记观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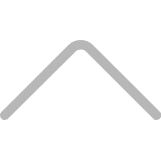
发表评论 取消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