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书架上有一本英文原版书《 Magic Cancer Bullet: How a Tiny Orange Pill is Rewriting Medical History 》*。获得这本书的时候,我还在诺华工作。而这本书的作者就是当时诺华的CEO, Daniel Vasella博士 。重新打开这本书是应为书中讲的就是最近红火的电影《我不是药神》中的焦点:首个抗白血病靶点药物-格列卫。
现在不少人在介绍格列卫时都把这个研发历史推得很远,包括最早发现"费城染色体"的故事。其实就这个药物的研究本身来说,他的真正起点是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对抗肿瘤"靶点药物"激酶抑制剂的研究热潮。而它的成功也得益于90年代同步发展的高通量药物筛选技术。
虽然"费城染色体"发现得很早,但是它的分子机制要等到80年代中才搞清楚。当时美国Baltomore 和Witte教授在《科学》杂志上先后发表了关于他们的研究结果。 确认"费城染色体"导致了一个新的融合蛋白BCR-cAbl,而这个融合变异正是导致慢性髓性白血病(CML)的原因。他们的研究同时确认了这个融合蛋白是一个酪氨酸蛋白激酶 (Tyrosine Kinase, TK)。BCR-cAbl是当时研究的众多激酶靶点中的一个。但是由于它在是"费城染色体"所导致的慢性髓性白血病(CML)中唯一的一个基因变异,也成为了最受关注的靶点之一。
cAbl 的得名来自于它和从实验室老鼠中分离出来的一种病毒(v-Abl)序列的相似性。v-Abl在老鼠中可以导致鼠白血病(Murine Leukemia)。 人的Abl基因也非常有可能来自病毒,但现在已经是我们基因组的一部分。Abl基因的主要功能是参与细胞分裂,分化,粘连以及细胞应急反应等。 但是如果这个基因发生变异或者被过度激活,也可以导致细胞无序生长,也就是癌症。因此这类基因也被称为"癌原基因"(proto-oncogene)。为此,Abl基因也通常写成 c-Abl。这小写的"c"指的就是它的癌原性。
BCR是最终融合蛋白的"另一半"。它的全名是"断点簇区蛋白"(breakpoint cluster region protein)。BCR本身也是一个激酶。在著名的"费城染色体"的情况下,9号染色体末端的c-Abl基因移位(Translocation)并融合到22号染色体的BCR上去了。而这个"跨越时空的结合",永久性地激活了cAbl,并由此导致了CML。BCR-cAbl 的发现不但解释了"费城染色体"以及CML的发生原因, 也为肿瘤药物研发提供了一个新的分子靶点。 而研发针对BCR-cAbl的抗肿瘤药物的历史大任就落在了被电影所暗批的诺华制药的几名科学家,Alex Matter博士等人身上。

Alex Matter 是一个医学和哲学双博士,从小就崇拜巴士德和居里夫人这样的科学家。在开始研究职业生涯时,他就发誓要做出对世界有贡献的工作("to make an impact on the world"),尤其是在癌症治疗方面。但是就在 Alex开始他的研究时,他所工作的国际制药公司Ciba-Geigy因为投入太大,收获太少,决定关闭其肿瘤药物研发部门。而Alex不得不跟随他的导师 Peter Dukor博士在公司中勉强维持着一个很小的肿瘤药物研究小组。 但是这一切并没有改变他对于新抗癌药物研究的热情或者说"疯狂"(craziness)。在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他在激酶抑制剂方面的研究逐步显露头角,以及整个医药界对激酶抑制剂的关注,大风终于起来了。他的研究队伍也逐步扩大了。在高峰期,Alex领导的实验室扩大到100个研究人员。而这个团队的研究成果就是世界上第一个成功的抗肿瘤"激酶抑制剂"(Kinase Inhibitor):格列卫(Gleevec)。
格列卫从研究到临床乃至最后获得上市的过程也是"一波三折"。首先是公司市场部门不愿意推动这个药上市,主要是考虑到患者人数太少。对于诺华这样大的一个国际制药公司,市场如果太小,公司是难以盈利也难以支持以后的新药研发。在真实世界里,制药公司绝不是像电影中很多人想象的那像,都是张着"血盆大口"在赚钱。根据德勤公司2017年的报告**,制药公司研发成功一个新药的投入从2013年的10亿美金增加到2017年的21亿美金。 而一个成功的"大药"(blockbuster)在高峰期的销售却仅仅在10亿美金左右。因此制药公司在研发上投入的回报远非常人想象的那样高。如果考虑到所有中等以上医药公司,这个回报率在2017年大约为10%。而如果仅仅考虑到大型医药公司,这个回报只有3.2%。要是拿中国人熟悉的一个公司做比较,这就是一个"小米"价。 医药公司回报如此之低,除了研发费用外,平均10个临床试验中只有一个可能成功。医药公司和患者最终也都需要为失败"埋单"。
但是在看到格列卫临床前实验结果后,诺华的管理层还是做出了正确的决定,将格列卫推向临床,而将"是否盈利"的问题留给将来考虑。然而在获得美国FDA批准进入临床研究后,诺华公司居然找不到一个临床医生愿意承当这个任务。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格列卫所针对的疾病CML在当时有标准的治疗方法。因此一般人都不愿意试验一个机制完全未知的新药。最终创新团队说服了刚刚从达纳-发博肿瘤研究所出来,参加俄勒冈州健康科学大学(OHSU)的 Druker博士担任临床首席,并通过Druker 博士邀请到加州洛杉矶大学的 Sawyers 博士和德州大学 MD肿瘤研究中心的 Talpaz博士组成了临床"铁三角"。从1998年六月到1999年四月,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临床一期试验证明患者在使用格列卫后,淋巴细胞数目全部下降,其中1/3的病人体内具有"费城染色体"的细胞全部消失。临床试验取得意想不到的成功。
接下来的故事也非常正能量,大量的病人要求进入二期临床实验,由于原定人数有限,有些病人还为此发动"签名运动",最后诺华接受的试验人数大大超额。而诺华公司也为此加快和扩大了药物生产。而这一切都是在无法确知是否可以最后盈利的情况下开展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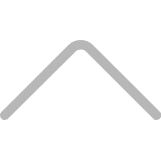
发表评论 取消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