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麻省理工科技评论》11 月 29 日的报道,来自美国哈佛大学的科学家 Werner Neuhausser 对基因编辑技术的科研应用提出了他自己的研究意向,并计划于几周内开展实验。他曾在今年 10 月到访中国,探索在中国研究胚胎的可能性。
Werner Neuhausser 希望,通过 CRISPR 技术对人类精子进行编辑,修改精子的 ApoE 基因,进而减少新生试管婴儿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风险。Neuhausser 及他的团队暂未与中国任何组织或个人达成项目合作。同时,他强调在自己目前的计划中,并不包括婴儿出生这一目标选项。这位来自奥地利的不孕不育专家仍旧对生殖细胞的基因编辑持乐观和开放态度。
他预测,在不久的将来,人们会在怀孕前对胚胎进行深入的分析、筛选,甚至使用 CRISPR 技术进行编辑。未来,人们可以在诊所完成基因组检测,并获得最健康的孩子。“很可能整个体外受精领域的重心将从生育转向疾病预防。”
对于 CRISPR 断开 DNA 双链进行基因编辑所可能带来的不确定性,该研究团队选择了“基因魔剪”的升级版——碱基编辑。该技术由同样来自哈佛大学的 David Liu (刘如谦)教授开发,这种编辑方法并不需要剪断双链,而是直接对单个碱基进行更改,进而将可能引入的编辑错误风险降到最低。
可就在 Neuhausser 及他的团队即将开始实验之际,12 月初,美国生命科学界收到一则消息:特朗普政府要求受雇于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科学家停止获取新的人类胎儿组织用于实验。NIH 官员表示,禁令直接影响到 NIH 的两个实验室,并且其中一项关于艾滋病病毒最初如何在人体组织中“定位”的研究更是直接被中断。
这一禁令的催化剂显然是最近公布的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基因编辑婴儿的诞生迫使整个学术共同体直面胚胎编辑问题。在 11 月 29 日于香港举办的第二届人类基因组编辑国际峰会上,多名学者一致表示,现在正是为胚胎基因编辑临床试验制定严格、负责任的转化途径的关键时刻。
有所为,有所不为
随着人类将基因与性状联系起来,越来越多的疾病开始被认定为基因遗传疾病。目前已经确定的单基因遗传疾病超过 6600 种,并以每年数十种的速度递增。在人群中,大约每 10 个人就有一个人携带了至少一种单基因遗传疾病的致病基因。
但携带不等同于致病,对于一些常染色体隐形遗传疾病来说,当父母双方均携带有致病基因,孩子就有可能患病。这种巧合是不幸的,人们希望用科学的工具进行“纠错”,改写生命,而 CRISPR/Cas9 就是这样一种可以对基因进行编辑的强力工具。
识别目标序列,进行 DNA 双链切割,凭借精准的切割和低廉的成本,近年来 CRISPR 成为基因编辑技术的主流,几乎席卷整个生物界,被应用于农业、医疗、临床等方方面面的前沿研究中。
但 CRISPR 并不完美。精准的识别和切割并不意味着完美无瑕,脱靶效应使这个过程变成了一个“黑箱”,在 CRISPR 的“作业”过程中,会发生什么,编辑效率会是多少,谁也不知道。
不仅如此,人类虽然在不断的认识自我,但从未做到认清自我。我们远比自己想象的更复杂,绝大多数情况下,基因与性状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这就意味着任何一个基因的增或缺都可能有着意料之外的影响,牵一发而动全身,因而在有万全的把握之前,没有人愿意、也不敢拿人“赌一把”。
即使是顾虑重重、饱受争议,但基因编辑这项技术却是真实且具有价值的。更不可否认的是,这项技术最终会被应用于人类。
事实上,人类已经开展了体细胞编辑的临床试验,2017 年 11 月,美国完成了首例人类活体基因编辑实验,目标是治疗一种叫做“亨特综合征”(Hunter syndrome)的代谢性疾病,这是一种由于基因突变导致的遗传性疾病。而就在 一周前,美国 FDA 又通过了另外一项关于先天性黑朦病患者基因编辑的临床试验。
与在体细胞基因编辑方面形成开放的共识不同,生殖细胞一直是一个颇具争议的话题。对生殖细胞进行基因编辑,意味着这种修改将会随遗传信息传递给下一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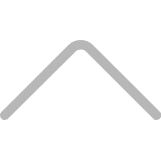
发表评论 取消回复